如果一个人应该像是一朵花,冰心曾评价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花,正如花有色、香、味,而梁实秋则才、情、趣兼具。《送行》至今仍是佳话,不同的笔者对于送行有不同的诠释。不同的解读也会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,意在讽刺虚荣的人心和虚伪的世象。“远行的安慰”亦是本源。
麦克斯·贝波姆的《谈送行》风格隽永、充满幽默与反讽,开篇即随笔,收录于散文集《甚至现在》。该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探讨了送行这一社交仪式的荒诞与温情,展现了其作为英国著名讽刺作家的独特洞察力。
贝波姆臆想出了一位“送行大师”角色,与自称“送行菜鸟”的笨拙形成对比。他能在送行时滔滔不绝,亦能让远行者感激涕零,而他自己却总在尴尬沉默中懊悔。通过这种对比,他暗示社交能力或许是一种天赋,但过度娴熟反而显得虚伪。
贝波姆的笔调以幽默和反讽著称,但正是这种轻松的外衣,使得内里的悲情更加真实和耐人寻味。他并非直接抒发哀伤,而是通过对人性弱点的精准解剖,给人一种淡淡的、普世的悲凉感。
孤独的必然性与交流的徒劳
最真挚的不舍往往迟来,当新的旅途开始,对方的孤独才愈发猛烈,变得真实。” 这种情感上的不同步,使得最浓烈的感受只能由个人独自咀嚼,无法在送别那一刻与对方共享,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孤独。
在现实生活当中,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让位于表现的得体性。
时间流逝与存在之惘
送行是时间流逝的一个尖锐刻度。火车的移动是时间不可逆转的具象化,站台则成了人生一个个“过去”的节点。
贝波姆笔下的悲情,不是嚎啕大哭的悲剧,而是一种温和的、智慧的哀愁。从外显的行为和冷静的观察当中我们不难看出:
其一,克制与含蓄:他从不滥情,悲情是通过反讽、自嘲和精细的观察间接流露的,因而更显深刻。
其二,普遍性:他描写的不是个人的巨大不幸与迷失,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或正在经历的、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失落,因此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。
其三,幽默作为载体:幽默像一层糖衣,让内含的悲情不具备苦涩,但回味起来,余味却更加悠长。读时令人发笑,读后却让人陷入沉思,感受到一丝说不清的惆怅。
《谈送行》中的悲情,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冷静观察:是当下的我们渴望连接,却注定孤独的内省;是我们努力表达,却总显笨拙的总体展现;我们对抗时间的流逝,却在不觉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它的存在。贝波姆以他优雅而略带伤感的笔触,让我们在笑声中,触摸到了生活本质里那抹无法驱散的凉意。

与此不同的是,梁公的文风,笔法细腻独到,比喻生动形象,视角出人意料,文字表现力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入木三分。结尾的戛然而止,耐人寻味如欧·亨利的小说。虽说窥一斑可见全豹,但读此文,实在难以取舍。
皮克.菲尔《送行》一文中巧妙运用漫画式的笔触揭示出了人性当中的孤独,强烈的对比切合文章的真实意图。所谓“断肠人在天涯”,“我们”分别的时间愈长,孤独感自然越发强烈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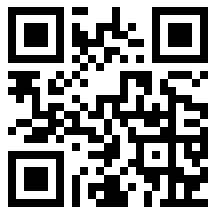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